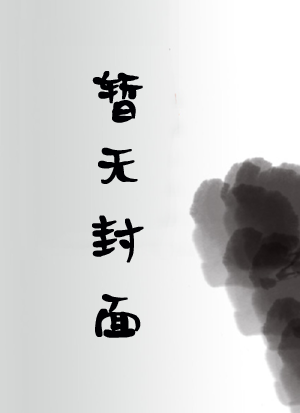"
“哦?”段达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,目光似有深意地投向杨桐,微微欠身,缓声道:“陛下有何良策,可解我军困厄?”其言语虽恭敬,然那眼神之中,却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与试探。
塔读@ 满朝文武之俸禄,于王世充与段达而言,不过是疥癣之疾。众臣多出身世家,富埒陶白,此二人岂会将发放俸禄之事萦怀。然其麾下将领,犹如芒刺在背,不可轻忽。犒赏诸将所需资费,甚于豢养二十万大军,且关东之地,局势纷扰,民生凋敝,欲维持此二十万淮泗军之军需,亦属不易,朝廷开支,亦非独军费一项。 王世充与段达,绝非愚鲁之辈,岂不知竭泽而渔之患,终会殃及自身。然其深陷泥沼,无奈之下,唯有加税一途可觅。当此乱世,兵权在握,方能于这风云变幻之局中占得一席之地。一旦失此二十万雄兵,莫说抗衡天下诸侯,即洛阳城中各方势力,亦能将其玩弄于鼓掌之间,令其死无葬身之地。故于兵权一事,纵令关东膏腴之地化为荒墟,亦绝不退让分毫。 此刻闻杨桐有应对之策,众人目光如炬,皆齐聚于这位年仅十岁却身系天下的幼帝身上。虽心存疑虑,然皆欲先闻其详,再作计较。 不单王世充、段达,朝堂之上,卢楚、司马防、封德彝、马姚等重臣,亦皆瞩目杨桐,目光交错间,似有暗流涌动。杨桐顿感压力如泰山压顶,几欲窒息。 杨桐心中暗自叫苦不迭,虽来此世间已然有时,然身为傀儡皇帝,与市井底层仿若隔着天渊。梦境之中,孙武虽传其治国大略,然多为驭人、控局与观势之宏观大道,至于民生庶务之细微,却只字未提。 诸般目光汇聚,仿若重重迷障,杨桐忽觉,即令身处梦境战场,直面千军万马之杀伐,其压力亦难及此刻百官目光所带来之威压。 然其思绪飞转,此困局于当世,非独关东独有,中原诸侯亦多深陷其中,苦无良策。毕竟乱世之中,无兵者犹如待宰羔羊,纵有繁荣盛景,亦不过是他人觊觎之肥肉。杨桐恍惚忆起李渊似曾困于此境,且得以解脱,然具体应对之法,却如水中月镜中花,难以捉摸,只觉头脑混沌,燥热难耐。 群臣见杨桐久未言语,眉头渐蹙,疑虑更盛。 “屯田!”正值王世充欲出言讥讽之际,杨桐脑际仿若灵光乍现,脱口而出:“对,便是屯田之策。” 众人皆愕,旋即疑惑地看向杨桐。卢楚眉梢微挑,轻声道:“陛下有所不知,如今我关东之地,赋税之苛重,已然超于屯田所获之分成。即便招募流民屯田,恐亦难挽颓势,收效甚微。” 原文来自于塔&读小说~& 屯田之制,源起于秦。昔日始皇帝遣蒙恬率十万虎狼之师北御匈奴,为保前方军需无虞,且免国力耗损过剧,遂自河南而北,临河筑垒,募流民垦荒,以为十万大军之后勤根基,此乃屯田之雏形。 文帝之时,匈奴益强,为御其南侵,移民实边,亦师先秦屯田之法。然彼时屯田所出,并非尽入国库,乃与屯民分利。依汉律,借官府耕牛者,官民六四分成;自备耕牛者,则五五均分。而如今关东赋税,竟高达八成之巨,此非寻常屯田之法可解之困局。 “朕所言屯田,与卿之所言略有不同。”杨桐此时心中已然有了几分计较,沉声道:“朕所倡者,非民屯,乃是军屯。” “军屯?”王世充双眉一挑,目光中满是疑惑与警觉,直视杨桐。 “正是军屯。”杨桐神色笃定,决然点头道:“朝廷可拨出国有之地或荒僻之壤,令将士耕作,所获尽归军队所有。” 卢楚目光一闪,此策甚妙,恰似一把无形之刃,可暗中削弱王世充等人之军权。 “若将士皆事农耕,谁来戍守疆土?此议不妥。”王世充却冷哼一声,面现不悦,直言反驳。 杨桐遭其顶撞,心中愤懑,然形势逼人,唯有强抑怒火,耐心解说道:“可使将士分批轮作,一部耕耘,一部操练,定期交替。朕知关东二十万大军,并非皆司戍边之责,与其令其闲逸生事,不若使其劳作,一则可防将士滋事,二则可自给自足,纾解朝廷重压。” “陛下所言甚是。今朝廷赋税过重,关东诸郡百姓纷纷举家南迁,长此以往,不出三年,关东必人烟稀少,田园荒芜。彼时莫说加赋,即赋税提至十成,然无人耕种,将军又何以为军粮?”马姚出列,面带微笑,侃侃而谈。 “这……”王世充语塞,段达亦陷入沉思,默默不语。 原文来自于塔&读小说~& “国以民为本,若条件许可,朕以为,可酌减两成赋税,一可解百姓倒悬之苦,二可招徕流民归附。”杨桐神色从容,缓声而言。他虽不知隋朝末年天下人口几何,然曾闻卢楚所言,整个关东之地,人口总计尚不足三百万,相较后世一二线城市之人口规模,实乃天壤之别。 虽此时代人口难与后世相提并论,然偌大一州,人口如此寥落,亦令杨桐心生寒意。倘若王世充、段达果真加税,诚如马姚所言,不出三年,关东必成荒土。届时即便己身能除王、段二人,重掌大权,然面对此等荒芜之地,莫说平定四海,即自保亦成奢望。 “不行!”杨桐话音未落,王世充不假思索,断然拒绝,军屯之事尚无定论,减税之说,绝无可能。 杨桐心中暗咒,然此刻唯有隐忍。今日之事,若能促成军屯,已属不易。至于减税,唯有徐图良策。 朝堂之上,顿时鸦雀无声,卢楚等人面色铁青,怒目而视王世充。此人竟敢如此无礼,屡屡冒犯陛下。陛下纵有差池,亦不应如此张狂。若非有所忌惮,卢楚恨不能拔剑而起,立斩此人。 王世充却浑然不惧,对朝臣之怒目相视视若无睹。军屯已是其底线,减税之事,绝难应允。 段达见状,出班躬身道:“军屯之事,不知陛下可有详策?” 哈? 杨桐微微摇头,此不过临时起意,何来详策?莫说军屯,即屯田之细务,亦不甚了了:“朕方才仓促所思,尚无详章。卢大夫精于政略,此事可委其全权处置。” 卢楚略作踌躇,此事若有差池,必两头受气。然杨桐既已开口,自不能如王世充般顶撞,且若成此事,或可为关东留存元气,待日后陛下亲政,局面亦不致崩坏。遂点头道:“老臣自当殚精竭虑,不负陛下所托。” 原文&来~自于塔读小~说APP,&~更多.免费*好书请下载塔~读-小说APP。 “将军意下如何?”杨桐虽心有不甘,然深知洛阳城中,己之政令欲行,王世充、段达乃必越之障,唯有向其问计。 “也罢。望卢大夫速办,否则,唯有加税一途。”王世充冷然道。此事非其所长,麾下亦无良策之人,唯有仰仗诸臣。此亦其掌控关东大局,却未对世家动手之因由,非不欲为,实乃离此等人,关东必乱如散沙。 “王将军放心,老夫自有定夺!”卢楚闻其言外之意,亦冷哼以对,淡然回应。 “既如此,若无他事,退朝罢。”杨桐轻挥衣袖,面沉似水。 “臣等恭送陛下。”朝臣纷纷行礼,待杨桐离去,方各自散去。 杨桐面色阴沉返回乾阳殿,直至寝宫,神色方稍缓和。减税之事,非不欲为,实难达成。自始至终,其志唯在促成军屯,阻王世充、段达加税之念。赋税已高达八成,若再攀升,纵冒奇险,亦必除二人。 今虽得行军屯,然百姓流失之势恐难遏止。若非万不得已,杨桐实不愿涉险。其心中忖度,若杀二人,此二十万大军或分崩离析,各为其主,甚者或为争己而混战不休。如此,则己掌大权之望,微乎其微。 至于减税之事,唯有待机而动,从长计议。